Ecological Restoration with Loc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Expressway-Crossing Regions of National Park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
摘要: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唯一分布有高速公路的国家公园。高速公路穿越段地处乡村,地形与景观复杂,需要当地社会化参与,才能顺利开展长期监测和全面的生态修复,有效防控道路带来的景观破碎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野外实验和实地调研,研究发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高速公路穿越段稍有景观破碎化、生境隔离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环境问题,以及该区域以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为主的常住人口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公园建设发展不平衡等社会现状。在此基础上,建议建立政府主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修复机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等以志愿服务、科学研究、资本参与等形式,在高速公路穿越段的关键区域(如河流与农田附近)修建收集道路径流的沉淀池与人工湿地,降低道路径流对周边带来的重金属与富营养化污染;增设高架林地与下穿涵洞等生态廊道,提升高速公路两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景观连续性。同时,借助高速公路的交通便捷等优点,挖掘高速公路穿越段的黎苗传统文化,整合纳入周边景区的规划,发展生态旅游和研学教育,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社会化参与的生态修复能够有效组织、发动当地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修复,实现可持续的环境治理,以期促进乡村振兴、国家公园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Abstract: Societal participation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ecosystem st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national parks, while promoting the public unity in building the national parks. National Park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is the only national park in China with expressways. Through literature collection, field surveys, and investigation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xpressways had caused ec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habitat isolation 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 degradation in the park, and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with Li, Miao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has been unbalanced with the park’s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park.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we suggested establishing a government-led and public-participate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chanism. We can encourage and guide societal organizations, experts, scholars and enterprises to build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recovery the key areas (i.e. secondary forest, artificial forest, river, and farmland) in the expressway crossing section of the park by voluntary servi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apital participation. We can also guid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Li and Miao based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logy, develop eco-tourism and research education, mobilize public enthusiasm,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mprove public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jointly participate i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he National Park.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保护着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1-2]。对国家公园进行生态修复能够有效保护和恢复其生物多样性,维持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从而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促进区域生态安全良好格局的构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3]。
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注重严格的生态保护和共建共享[4-5]。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6],明确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国家主导,共同参与”的原则,要探索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探索社会力量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新模式。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社会化参与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刘道平等[7]建议在国家公园管理上,强化社区居民、准入企业、专家学者等公众参与内容和参与途径;窦苗等[8]鼓励公众参与国家公园生态管理;孟耀等[9]提出将社会化参与和科普教育相结合,探索高质量的自然保护地全民共享机制。然而,鲜有学者系统地提出社会化参与的生态修复方式,解决长期的资金、技术与人员的投入问题,实现国家公园内受损或退化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恢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保护着我国分布面积最大、最集中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保存着独特的黎苗文化[10]。然而,2018年年底全线通车的海南岛中线高速公路,自东北—西南方向穿越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影响了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可能存在潜在的生态风险[11]。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速公路穿越段已出现了一定的土壤污染、水体污染、景观破碎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以及治理模式单一、社区参与度较低、保护与发展矛盾较为突出等问题[11-12]。道路生态系统恢复,特别是高速公路的生态系统恢复,本质上是实现植被的恢复,以发挥水土保持、清洁大气和降噪等功能,以护坡工程、植被恢复与重建为主要手段[13-14],但受资金、专业技术、人员等因素影响,后期养护不足,极易造成“一年绿、二年荒、三年变成老模样”现象[15]。因此,对国家公园实施社会化参与的可持续性生态修复迫在眉睫。
1. 研究区概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和世界保护优先生态区[16-17],也是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在全球范围唯一的栖息地[18]。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分布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世界热带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19-2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具有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据估算,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陆地生态系统涵养水源量为38.7亿m3,约为海南全省2019年用水量的83.4%,固土和保肥分别为648.01万t和30.78万t,固碳和释氧分别为175.39万t和473.73万t[19]。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海南3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区[21],也是海南岛最大的2座水库(松涛水库和大广坝水库)的主要水源地,被称为海南岛“三江源”和“水塔”[19]。
2. 高速公路穿越段的环境现状
2.1 基本概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目前唯一分布有高速公路的国家公园[12]。该高速公路(G9811)于2015年(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之前)开始建设,在2018年年底全线贯通,路宽约26 m,双向四车道设计,穿越了海南岛的中南部山区[12](图1)。高速公路打通了海南中部山区的交通大动脉,为海南省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了运输保障[22]。
这条高速公路穿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路段(以下简称“高速公路穿越段”)北起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南至五指山市番阳镇,全长约40 km (图1)。高速公路穿越段先后6次跨越昌化江(图2A)、多次跨越村庄(图2C)和农田(图2D)。高速公路穿越段的植被类型主要包括水田和耕地、次生林(热带雨林次生林和季雨林次生林)、人工林(橡胶林、槟榔林、果林等)、水域等(图1)[11]。
2.2 景观破碎化
研究结果发现,高速公路穿越段的景观形状指数、斑块密度指数、聚集度指数最大影响范围达到了500 m,高速公路附近的有林地、草地面积减少,其他林地(含果园)面积增加,人为活动影响明显[12]。
高速公路穿越段分布着什运乡、毛阳镇、番阳镇等人口聚居点,建设用地和各类道路分布较多,破碎化程度较大,存在较高的生态风险[11-12](图1)。高速公路穿越段内的隧道和高架桥路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景观连续性,可以较好地维持两侧的生态系统连通性,因此,这部分路段的景观破碎化程度较小[11]。
2.3 生境隔离
高速公路穿越段26 m的路宽,对两侧的植被和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的物理隔离,极大地改变了路侧生境,车流噪音、风向改变以及道路两侧污染物的积累,均可能进一步造成道路的生态隔离效应,阻断扩散能力弱的物种(如两栖爬行类、草本植物等)迁移与基因流。前期研究发现,海南岛特有植物盾叶苣苔(Metapetrocosmea peltate)、烟叶报春苣苔(Primulina heterotricha)以及马铃苣苔属(Oreocharis)植物在高速公路穿越段(昌化江河谷)的两侧发生了显著的遗传分化[23-25]。
因此,高速公路有可能与昌化江河谷共同形成了更大强度的隔离作用,限制了这些植物的扩散与基因流,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加剧高速公路穿越段两侧的生物遗传分化,与景观破碎化效应一起影响到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
2.4 生态环境质量略有下降
研究结果发现,高速公路穿越段两侧的土壤重金属镉、铬、镍、铅、铜和锌的含量均高于天然土壤的背景值,高值主要分布在距高速公路10 m范围内。土壤镉的地累积指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在高速公路两侧10 m范围内均较高,呈现无污染到中度污染、无风险到中度生态风险的环境。正定矩阵方差分析显示,由于高速公路主要通过降雨形成的道路径流冲刷道路重金属到路旁土地,从而增加了土壤重金属含量。昌化江水体的化学需氧量的含量低于15 mg/L,重金属含量较低,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暂未达到污染状态。但道路径流对来自车辆的有机物质、悬浮固体、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长期冲刷和渗漏[26],对昌化江水质可能带来潜在的威胁。高速公路穿越段正位于生态敏感的水源涵养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水源涵养与水质净化功能的核心地带(图1)。高速公路带来的水、土等方面污染的长期累积,可能影响到该区域水源涵养和水质净化功能。
3. 高速公路穿越段的社会现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涵盖五指山、琼中、白沙、昌江、东方、保亭、陵水、乐东以及万宁9个市、县,涉及43个乡镇175个行政村,其中有常住人口2.28万人。高速公路穿越段主要位于琼中县、五指山市的什运乡、毛阳镇和番阳镇,常住人口分别为0.57万、1.53万和1.02万,主要是黎、苗等少数民族。社区居民主要经济产业以种植水稻、槟榔、香蕉、绿橙、橡胶等为主,经济结构单一、增收渠道狭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海南省平均经济发展水平[27]。其中,五指山市、白沙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琼中县于2021年脱贫。
高速公路穿越段的当地居民主要是长期定居在此的原住居民,生活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多元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独具特色的雨林民族文化,包括“三月三”、绣面文身、打柴舞等风土习俗,船型屋、黎锦[28]、制陶、树皮衣以及苗族蜡染等传统技艺,以及鱼茶、“南杀”泡菜、山栏酒和竹筒饭等传统美食,并有黎苗歌舞、方言长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10, 29]。
社区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有较强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公园的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范围划定以及施行的生态保护措施,限制了社区居民对现有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区居民收入减少[30]。社区问题是国家公园在建设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大问题[5]。社会化参与的生态修复是建设国家公园和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权益的重要举措(图3)。
4. 高速公路穿越段生态修复的社会参与实践与探索
4.1 社区参与
为了更好地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鹦哥岭腹地的白沙南开乡高峰村110多户村民进行了生态搬迁。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除了少量经营橡胶林,大多数居民引进优质农企,以“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在橡胶林下种植红托竹荪。自2021年10月起,在帮扶部门及企业的支持下,新高峰村整合资源将菌菇种植基地的规模扩大至0.1067 km2,并动员村民积极投工、投劳,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新模式。
当地原住居民对当地植被历史、地形地貌、人文与村民沟通等具有先天优势,因此,建议在国家公园内开展社区共管,设置公益岗位,形成“国家公园+居民+N”的多项交流渠道,赋予地方社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增强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参与国家公园决策,加强监督[31]。例如,鼓励聘请当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原住居民作为护林员,参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保护国家公园穿越段的植被,并参与树种筛选、植被抚育、土地租用、临聘劳动力等具体工作,从而确保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和长期维护[32]。
高速公路穿越段周边分布着大量农田,传统的耕作方式导致地力下降,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建议引导原住民使用生物防治,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在专家和科技力量的参与下,社区居民应利用现代科技知识,挖掘区域农业发展的生态学原理,发展热带高效农业。例如,海南岛当地传统农林复合种植模式“木棉—稻田耕作体系”具有较高的景观旅游价值、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和经济产值[33],木棉根系又可以固持田埂、涵养水源,同时分泌根系微生物,减少秧苗病虫害。木棉花凋落于稻田中,快速分解,为水稻生长提供养分。木棉花大,既能吸引昆虫聚集,又能招来大量鸟类,捕食稻田间的害虫,有效控制稻田害虫的数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33]。木棉花、果、树均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社区居民可采用这一农林复合种植模式或类似立体化经济生产方式,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可提高经济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4.2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技力量支撑
在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中国工程发展战略海南研究院等资助下,海南大学联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针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速公路穿越段的两侧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水体水质、植物遗传分化与基因流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地研究了高速公路穿越段长期积累的污染及生境隔离效应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关键生态过程的可能影响,建立了样点监测高速公路穿越段的生态风险,并研究相应的生态恢复措施,以确保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的高标准完成[11-12]。
徐健楠等结合MCR 模型与重力模型生态模型和海南省国土二调数据,识别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重要生态源地,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公园内包括高速公路、大型社区等附近的重要生态廊道。海南医学院的曾念开等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开展了长期研究并在鹦哥岭分局建立了大型真菌监测平台,发现辣牛肝菌属[34]等60多个新物种的基础上,对主要大型真菌的经济价值及其开放模式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建议,促进了社区参与生态修复的积极性。臧润国等[35]运用生态关键保育和定向恢复技术、天然林结构优化调整等技术,推动了热带雨林的恢复改造,目前已完成示范面积0.144 km2,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霸王岭片区热带雨林次生林恢复缓慢、人工林生态功能低下等问题,并通过食源植物与生境恢复等实践研究,增加了海南热带雨林旗舰物种海南长臂猿的潜在栖息地面积。
4.3 政府参与和政策保障
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以来,海南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发布了一系列管理条例及管理办法,为国家公园保护和管理提供政策支持和司法保障。例如,2020年9月,海南省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36],提出坚持社会参与等原则,构建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主、各级人民政府配合、社会积极参与的协同管理机制;2020年12月,海南省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37],鼓励原住民利用自有或者本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房屋或受聘于其他经营者开展特许经营服务;2022年6月,海南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试行)》[38](以下简称《意见》),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司法护航。《意见》强调完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协调联动机制。尝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成果在生态系统修复方案、环境治理评估报告中的应用,可为保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提供更全面的实践经验。新形势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有助于实现穿越段社区乡村振兴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4.4 社会资本参与
道路的切割以及随之增加的人为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并且这种破坏具有长期效应[39]。经实地调研发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速公路穿越段目前仅有2处隧道的上方可以作为维持道路两侧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景观连通性的通道,但不能有效降低高速公路造成的生境隔离与破碎化问题影响[11-12]。此外,这2处隧道上方的植被均是橡胶林、槟榔林等人工林,生态系统结构不完善,生态廊道作用和水源涵养潜力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为有限[11]。因此,建议各区、县政府要明确相应部门或机构,通过科学设立并结合网络、报纸等多种渠道,及时向社会推介高架桥林地或下穿涵洞建设等生态廊道建设与恢复项目,按照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是合理可行的,确认并公布承担生态修复相关工作的企业、基金会或公众,并搭建中介服务平台。要充分利用高效和科研院所的专业优势,通过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对参与生态修复的社会单位和个人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鼓励本区域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修复。
针对高速公路两侧人为扰动较大的橡胶、槟榔等人工林,建议3种社会化参与的生态修复机制:一是半自然恢复。引入社会资本,置换经济效益较低、更新能力较弱的橡胶或槟榔林,并组织专家团队进行本底调查和科学试验,确定适合的乡土树种。通过补植本土树种、清除外来入侵物种、增加草本植物和植被层次与结构等方式,促进人工林的正向演替,逐渐恢复到半自然植被。二是发展林下经济。鼓励和号召社区居民在林下适度种植益智、牛大力等南药或者饲养禽类或小型牲畜,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三是引进专家团队。定期开展割胶等专业技术培训,提高人工林经济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高速公路的运营和附近居民生产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围河流和湖泊的水质。建议在生态脆弱区和敏感区域,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牵头,通过财政支持和社会资本,及时引进专业的团队,对道路径流等废弃物进行长期监测,并做无害化处理,拆除严重破坏环境的基础设施。同时,在关键节点,如道路跨越河流和农田等地区,建造收集与处理道路径流的沉淀池和人工湿地等,对道路径流进行收集与净化处理后,再排放到周边环境[11]。对于重金属含量超过本底值的土壤,可种植适宜的植物,吸收、富集重金属[3]。
4.5 宣传教育
国家公园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空间[40],社区居民在依靠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同时,也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27]。因此,需要加强政策法规等宣传教育,提升周边社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生态环保意识,从根本上保护和修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强调社区在生态旅游中的关键作用,能够充分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41]。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速公路穿越段周边的社区承载着丰富的黎苗文化和民俗风情(传统服饰、纺染织绣、节日活动、婚嫁丧葬),保持着真实的居住空间形态(船型屋等)。结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实地调研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生态学内涵,如黎锦的天然染料植物资源和染色工艺、船型屋构造的植物多样性及生态学原理等,深入挖掘非物质传统文化,将其打造成生态博物馆,引导居民开展有深度的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体验活动,激发村民保护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环境保护和社区协调发展。
同时,通过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社交媒体途径,宣传和推广国家公园雨林奇观、自然奥秘和黎苗文化等科普知识[41]。利用“世界生物多样性日”等特殊节日,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和周边雨林景区开展自然教育、生态科普和野生动植物观赏等活动,引领社会公众认识雨林、亲近雨林,增强全社会保护与修复国家公园的责任感,为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贡献智慧力量。
5. 结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目前唯一分布有高速公路的国家公园,高速公路穿越段周边与社区地域空间重叠或相邻,资源交错,出现景观破碎化、生境隔离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在引导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等社会力量进行生态修复的同时,还应加强周边群众参与社区共管、共建,发展生态旅游和研学教育,以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社会化参与的生态修复能有效组织和发动当地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公园的生态修复,实现社区和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促进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协调发展。
-
-
[1] Gaston K J, Charman K, Jackson S F, et al. The Ecological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The United Kingdom[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6, 132(1): 76−87. DOI: 10.1016/j.biocon.2006.03.013
[2] 黄宝荣, 王毅, 苏利阳, 等.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进展、问题与对策建议[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1): 76−85. [3] 何凯琪. 国家公园生态修复策略探析: 以南岭国家公园为例[J]. 园林与景观设计, 2021, 18(391): 161−166. [4] 关志鸥. 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EB/OL]. (2022-02-01)[2022-02-16].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2/01/c_1128312402.htm. [5] 孙鸿雁, 姜波. 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机制研究[J]. 自然保护地, 2021, 1(1): 72−79. [6]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EB/OL]. (2017-09-26)[2022-02-16]. http://m.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593966&page=1. [7] 刘道平, 欧阳志云, 张玉钧, 等. 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 机遇与挑战[J]. 自然保护地, 2021, 1(1): 1−12. [8] 窦苗, 陶玉柱, 谭琳, 等. 国家公园生态管理研究[J]. 自然保护地, 2023, 3(1): 67−75. [9] 孟耀, 陈昉, 李鑫, 等. 丹霞山科普教育社会化参与的探索与实践[J]. 自然保护地, 2021, 1(4): 65−71. [1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导览[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21. [11] 姚小兰, 周琳, 吴挺勋, 等.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速公路穿越段景观动态与生态风险评估[J]. 生态学报, 2022, 42(16): 6695−6703. [12] 吴挺勋, 姚小兰, 任明迅.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道路分布及其对景观完整性的影响[J]. 热带生物学报, 2022, 13(2): 101−111. [13] 金东日, 许东海. 公路路域环境生态恢复的若干问题探讨[J]. 现代交通技术, 2007, 4(6): 89−91. [14] 王倜, 陶双成, 薛铸, 等. 海南省高速公路路域生态系统恢复评价方法研究[J]. 公路工程, 2016, 41(1): 75−80,84. [15] 陈钰. 基于公路边坡生态修复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分析[J]. 交通节能与环保, 2022, 18(2): 145−149. [16] Myers N, Mittermeier R A, Mittermeier C G, et al. Biodiversity Hotspots for Conservation Priorities[J]. Nature, 2000, 403(6772): 853−858. DOI: 10.1038/35002501
[17] 马克平. 中国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Hotspot)评估与优先保护重点的确定应该重视[J]. 植物生态学报, 2001, 25(1): 125. [18] 杨小波, 陈宗铸, 李东海, 等. 海南植被志[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9] 陈宗铸, 雷金睿, 吴庭天, 等.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例[J]. 应用生态学报, 2021, 32(11): 3883−3892. [20] 张超.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森林健康评价及经营优化研究[J]. 热带林业, 2022, 50(1): 68−72. [21] Zhai J, Hou P, Cao W, et al. Ecosystem Assessment and Protection Effectiveness of a Tropical Rainforest Region in Hainan Island,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8, 28(4): 415−428. DOI: 10.1007/s11442-018-1481-1
[22]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琼乐高速建成通车 中国交建参建[EB/OL]. (2010-10-08)[2022-08-24]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4/c9665008/content.html. [23] 李歌, 凌少军, 陈伟芳, 等. 昌化江河谷隔离对海南岛特有植物盾叶苣苔遗传多样性的影响[J]. 广西植物, 2020, 40(10): 1505−1513. [24] 邢婀娜. 海南岛特有植物毛花马铃苣苔的保育遗传学研究[D]. 海口: 海南大学, 2018. [25] Ling S J, Qin X T, Song X Q, et al. Genetic Delimitation of Oreocharis Species from Hainan Island[J]. PhytoKeys, 2020, 157: 59−81. DOI: 10.3897/phytokeys.157.32427
[26] Wada K, Simpson R, Kishimoto N, et al. Motor Vehicle Wash-off Water as a Source of Phosphorus in Roadway Runoff[J]. Journal of Water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y, 2020, 18(1): 9−16. DOI: 10.2965/jwet.19-047
[27] 柴勇, 余有勇.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创新路径研究[J]. 西部林业科学, 2022, 51(1): 155−160. [28] Rahimullah M, SayokAlexander K, Ahi S, et al. Growth of National Parks Information Knowledge for Improv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Bangladesh: An Outlook on Policy Perspectiv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 2017: 1687-9368.
[29] 李霖明, 汤海宁, 符杰雄, 等.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黎族天然染料植物资源多样性及其利用[J]. 热带农业科学, 2021, 41(11): 33−44. [30] 李佳灵, 秦荣鹏, 徐涛, 等.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能力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J]. 热带林业, 2022, 50(2): 73−76,72. [31] 吴必虎, 李奕, 丛丽, 等. “国家公园负面清单管理”对我国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战略的启示[J]. 自然保护地, 2022, 2(2): 9−21. [32] 张志国.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珍贵自然资源传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J]. 绿色中国, 2021(20): 42−49. [33] Wang W J, Wen J, Xiang W Q, et al. Soil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ie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Bombax ceiba (Malvaceae) during Reproductive Stages of Rice in a Traditional Agroforestry System[J]. Plant and Soil, 2022, 479(1): 543−558.
[34] Xu C, Liang Z Q, Xie H J, et al. Two new species of Chalciporus (Boletaceae, Boletales) from tropical China[J]. Mycological Progress, 2021, 20(12): 1573−1582. DOI: 10.1007/s11557-021-01753-1
[35] 中国绿色时报. 中国林科院示范项目助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森林修复[EB/OL]. (2022-01-13)[2023-03-11]. http://www.forestry.gov.cn/. [36]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N]. 海南日报, 2020-09-06(A06). [37]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N]. 海南日报, 2020-12-14(A12). [38] 中国日报网. 海南高院出台司法服务和保障意见护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EB/OL]. (2022-06-28)[2023-03-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887095198901783&wfr=spider&for=pc. [39] McGarigal K, Romme W H, Crist M, et al. Cumulative Effects of Roads and Logging on Landscape Structure in the SanJuan Mountains, Colorado (USA)[J]. Landscape Ecology, 2001, 16(4): 327−349. DOI: 10.1023/A:1011185409347
[40] 张进伟. 国家公园与社区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0(9): 113−114,3. [41] 毋茜, 傅国华. 生态旅游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自然保护地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21, 49(16): 97−102,129. -
期刊类型引用(3)
1. 江悦馨 ,杨小波 ,梁彩群 ,王重阳 ,李婧涵 ,张顺卫 ,朱子丞 ,何亦绮 ,吴庭天 ,李苑菱 ,陈宗铸 .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天窗社区土地利用演变驱动力分析. 热带作物学报. 2025(02): 474-489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张哲,李亦祺,李匡宇,任明迅.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公路交通可达性. 国家公园(中英文). 2024(07): 447-455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王琼,伍业钢,任明迅,李百炼. 关于中国国家公园和国家自然保护区规划优化的建议. 科技导报. 2023(21): 14-2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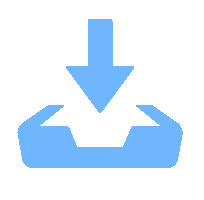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邮件订阅
邮件订阅 Rss
Rss